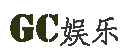残障题材电影回归烟火人间,撕开“他们”与“我们”的虚假区隔

更多的残障题材电影正突破过往的“冷门”或“公益”属性,向泛类型化领域深入。创作者们正在撕开“我们”与“他们”的虚假区隔,让那些特定特殊的生命经验,成为同样能照见普遍人的棱镜。
作者:杜桑
编辑:蓝二
版式:王威

不知你是否注意,关注残障群体的电影正在集体转型。过去,这类作品的创作多偏“样板化”,银幕上只见“笼统”的残缺,这个群体被困在需要小心触碰的苦难与励志叙事里。
而近几年,相关题材的视角,终于平视并深入他们生活中的真实与复杂。刚刚上映的《独一无二》即是近期的又一新例子。这部改编自法国经典《贝利叶一家》的影片,将故事移植到武汉烟火缭绕的鱼杂店。少女喻延作为听障家庭中唯一的健听者,既是无声世界与外界沟通的重要桥梁,又是渴望逃离亲情羁绊的叛逆少女。导演王沐剔除原作夸张的选举闹剧,转而用一场争夺老房产权的典型家庭纠纷,让听障父母与青春期女儿的冲突真实落地。
而这样的影片并非孤例:《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》让智力障碍球员用特殊战术逆转比赛,《小小的我》记录脑瘫少年用诗句叩击爱情,《不说话的爱》把抚养权官司变成手语辩护的舞台……这些电影不再刻意以悲剧性为重心,而是回归人间烟火的考验,在时代与现实的多元生活中,更细致地观察生命体验。
这场叙事变革,是让残障题材电影从边缘走向更大众的关键。由特殊性出发发现普遍性,它们试图令残障者的悲喜不仅仅是个人化的,也是更多不同群体在时代困局中寻找共鸣的切口。
细微,揭开日常的隐形创口
清晨的旧楼天台,脑瘫少年刘春和颤抖着掏出纸笔,用颤巍巍的双手衬着平静的神情写下遗嘱——这是《小小的我》开篇颇具冲击力的场景,摇晃的镜头与急促的呼吸声中,观众被拽入他最具体的日常中:倾斜的地平线在蹒跚脚步下剧烈震颤,公交车台阶化作需要攀爬的悬崖,便利店门帘成为必须侧身挤过的障碍。这不是对残障者姿态的猎奇展示,而是用身体丈量“普通人”这样平凡的词汇之中,已含有的幸运。
这些新的残障题材影片,以自己的细腻,去更理解地揭开那些藏匿于日常的隐形伤口:遗嘱信笺上的扭曲字迹,或者是法庭席位上拼命舞动却无人解读的手语,也可能是家庭餐桌前被迫放下的凉透的汤碗,这些镜头细节聚焦着残障群体的细微困境。

如果说这种日常的困境展示在这类创作的必要性不言而喻,那么作为高潮的小切面爆发更弥足珍贵。《不说话的爱》中的高潮法庭戏,用强情绪的爆发,在法律和亲情之间扩大了聋人父亲的现实难题。基于听障所面对的信息障碍,影片用上了声画分离的技法,将法槌敲击与法官质问消解为真空,听障父亲的手语动作在寂静中被放大成绝望的舞蹈,健听人所信赖的严肃司法程序,在这种交流的障碍面前变为无力。

对困境的极致呈现,在《独一无二》的听障家庭晚餐中蜕变为更隐蔽的暴力暗示,健听女儿喻延游走于学校的重压和家庭的生机之间,家庭小店对外手语翻译的重担,一定程度上将她异化为了“传声器官”,而父母对其音乐爱好和发展机会的忽视,让这种青春期的无助在“血脉亲情”、“弱势群体”的裹挟中被不断放大,这些创伤伴随着家庭伤口的撕开在观众心里隐隐阵痛。
可以看到,这些新的残障题材创作,从日常性、戏剧性、隐喻性等更多切面,进行着对残障人群生活境况更纵深的挖掘,以此为观众建立起新的理解与认知。

新解,在类型化和诗意中重构尊严
当撕开日常困境的创口后,真正的叙事变革才刚刚开始——那些曾被悲情叙事遮蔽的生命力,正在类型化叙事的土壤中破土重生。
创作者们以喜剧的荒诞、诗意的隐喻、类型的越界,将残障人士还原为拥有完整情感光谱的人。这种创作转向暗含着一个尖锐的叩问:当我们谈论残障者时,为何总在讨论他们“如何克服缺陷”,却从不追问“我们如何重构看待缺陷的视角”?
《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》作为为数不多的相关喜剧类型,其创作逻辑可谓提交了一份自己的类型答卷。影片巧妙地运用喜剧性,让观众迅速建立起对智力障碍群体的情感认同。在篮球场上,智力障碍球员面对大比分的落后,他们用“滑稽”的算术问题和“荒诞”的战术赢得比赛,随着观众笑声取代眼泪成为叙事催化剂,传统励志叙事的逻辑也在进一步“松绑”。在大众化的“竞争强者”语境中,残障角色获得了对生命尊严和生命能量的重新塑造,使得银幕上的他们挣脱了悲情标本的宿命。

日常生活的诗意突围,则提供了另一种尊严重构的可能。李沧东的《绿洲》为我们铺设了教科书式的创作蓝本,影片通过仰拍的方式,让脑瘫女性扭曲的肢体在植物的光影中舒展为飞鸟,使压抑的情欲迸发出灼目的生命力。将往日的生理局限,转为身体美学的载体,在这样非常规诗意的视听烘托下,生理局限反而成为欲望书写的绝佳注脚。

而类型片的破壁实验,更彻底颠覆了残障者的叙事位置——就如《不说话的爱》,尽管部分的公益观感让影片一定程度上仍受制于苦情叙事,但由于犯罪类型元素的加入,其他犯罪电影里算不上“大题”的骗保,也让它有了新的类型活力。
值得关注的是,今年还将上映的《震耳欲聋》聚焦听障群体维权事件,《千金不换》以喜剧模式探讨自闭症儿童家庭伦理,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的相关题材正加速突破过往的“冷门”或“公益”属性,向泛类型化领域渗透。
从喜剧解构到诗意再现,再到类型化的创作取向,这些创作实践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:不再居高临下地将“身体残缺”视为要在故事中去“修补”的问题,而是重建平视叙事的逻辑与方法。当观众一以贯之的逻辑被打破,荒诞战术和手语辩护出现在银幕上,让观众认知中的残缺与完整的界限开始松动。这种松动带来的不是廉价的感动,而是对生命的多样态真正的敬畏。
连通,在普世性题目中创造共鸣
欲望书写的正当性,也是不可回避的核心命题。
作家史铁生曾在《病隙碎笔》中做出如此洞察:“残疾人的爱情所以遭受世俗的冷面,最沉重的一个原因,是性功能障碍”。而残障者欲望在影视创作中的空白,本质上是对人性完整性的破坏。
在近几年的作品中,李沧东在《绿洲》对残障男女的床戏毫不避讳展现其笨拙与渴望,早早定下了情欲与残疾绝非对立命题;《小小的我》则把轮椅少年情窦初开的笨拙,化作诗集里欲说还休的暗语;而在《独一无二》中,中年恩爱的听障父母也真实地表现出了情欲——这些无疑都是对“刻板”的深度打破。
当镜头不再回避残障者发烫的指尖与潮湿的眼神,那些被磨平成符号的生命,更加血肉丰盈。

在打通普世情感这一逻辑中,社会焦虑的同等投射更是一种打通认知的重要方式,这点在香港听障题材创作《看我今天怎么说》中得到了细致的体现。
影片聚焦三位聋人青年在不同的成长条件和身体状态下,面对生活和未来不同的心态和选择。这种“入世”的创作恰恰是打通普世情感的核心,在当下年轻人于躺平和内卷的抉择中求索时,残障群体并非与这些社会痛点隔绝,相反,正因为他们的特殊,所以他们关于入世的态度更显得可贵。创作者对这一层面的聚焦,或是影片在豆瓣拿下8.5高分口碑的关键,而这种突破无不印证着,唯有看到残障者与常人共享现实中的命题,才能真正实现叙事的回归。
当关注残障群体的电影完成困境理解与尊严重构的双重使命后,最终指向的并不只是特殊关怀,而是对时代命运与人性褶皱的深度勘探——那些被贴上特定标签的生命经验,恰是照见普遍人的棱镜。创作者们正在撕开“我们”与“他们”的虚假区隔,让轮椅上的情欲、手语中的亲情、点滴下的焦虑,都成为所有观众反观自我的镜像。

THE EN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