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东诸城八乡里社,修家谱、查祖籍、探地名必备,关注收藏备用。
诸城,名字说起来简单,背后可真不浅。早些年夏商时期,有个“诸”国在这片地头晃悠,到了春秋鲁国来了,秦汉又是琅邪郡、东武县一阵折腾。名字的变更和归属的变化说起来曲折,不是三言两语能交代清楚的,说是地理沿革,倒还有点像老街巷里头的家长里短,谁搬迁哪一户,谁又改门换姓。这历史,反正细节多得数不过来,蹉跎到隋代,才总算落了“诸城”这俩字。为啥叫诸城?归结起来一句话,借山得名,东武山嘛。细问下去,城墙根下的老辈子们谁也说不全,也不想纠结这茬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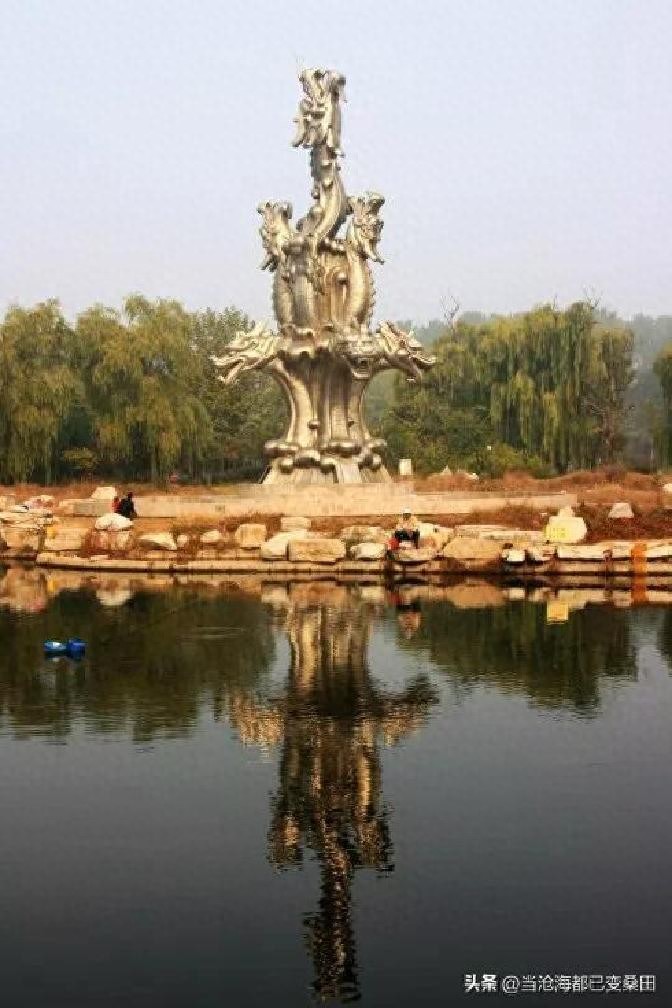
其实提起“里社”,跟现在讲社区有点像,别以为那么复杂。明代开始,就讲究一乡分好几社,社下分村。成天嚷嚷里社制度,其实就是数人头、分农田、派差役,都方便。那时候,一百多户为一里,十户出来推个头,年年服差役,没人愿意,那也得轮着。就像现在社区选个业委会主任,谁也不愿背锅,还不是得走程序?明万历年间,八乡里社框架搭得结结实实。甚至街坊传说,还能对着旧志起哄,八成都忘了那些里长、社名,倒是哪个村谁家茄子长得好、谁家墙头狗爱咬人,嚼得热闹。
翻明清的老志书,提这些社名、村名多得惊人,报恩乡的全人社、福胜社、崇兴社……顺河社、朱村社、山前社,细列出来是密密麻麻。文献里能找到村名的,多少还留了点传承的线索。比如顺河、潘旺、大王门、瓦店、焦家庄子、柴沟,各自在年代尘埃里扎了根。现在问,谁晓得报恩社里具体哪家刘姓发的财,十有八九没法对上号,只能靠地皮上的传说混个耳熟。

诸城的乡社制度,倒真不觉得比大城市的小区楼盘逊色。古人分乡八座,八乡底下三五十社,再下面又分小村,据明代的记法,名字纯靠地势走向或是靠个地名随便一取。有的社名是山水作证,有的则干脆因为有偏姓家族聚居,像是报恩社里东城后、西城后这种,隐隐带着一种地缘的顽固。那老街坊邻里之间,人情比地界还要分明。细览下来,有些村名已变,有些则虚无缥缈,成了族谱上泛黄的几页,其实谁都解释不清“消耗”是咋个意思,它不像水往低处流,一时盈一时缩。
有意思的是,细想那些村社的来历,乡下人城里人都喜欢编一堆轶事。比如大王门,诸城的王氏族源地,明清两代都来回在志书里出现。传到了新世纪,光一个社区,就有一堆名字。到了现代网络时代,地名变社区名,归属也跟着行政调整摇摆,那能怎么办?兴许谁家祖坟头还留着碑,才晓得大王门是王氏发家的地标。而村社的划分,外来人听起来拗口;本地老人提起,却都有故事传。

瓦店,说起就能扯半天。往南,邻着高疃,往东是潘家庄。管氏一族从海州搬来,说低洼就起个“凹甸”名,这好笑吧,结果谐音成了瓦店,甭说,挺贴切。过去那年月,赶集做买卖的多,也因交通便利,瓦店这小地头,倒是比旁边几个村子来得热闹。古往今来,农历逢三八都赶场子。全羊老汤锅,不试不知道,到了现场才晓得,诸城这类小集市能讲出多少奇闻。
其实这么说,诸城地区的社戏、社集习俗才是乡土生活的灵魂。鲁迅写“社戏”,其实道理一样,农村凑份子过春社,大村出戏班,小村合资捧场。赵庄、平桥,再大点的地方有演出,小村村民得出钱出人,难,谁也离不开谁。现在演变成广场舞、小区合唱,形式变了,本质没变。你问原来社戏为啥这么热闹?再有知识的人说得清?也许这就是一种仪式感,春天来了,总得有点热闹。

某种意义上,八乡里的分合、村社的兴衰,很像社会的呼吸一样起伏。风水轮流转,今天有村明日没人,旧志的“户口消耗”,其实就是移民、衰败,再繁华的社也可能变成荒草丛生的黄土垛子。柴沟,是个例外。高密、诸城两县分界,古时就治安混乱,甚至顾炎武都写到这里盗贼多,设区长把守。明清时叫柴沟社,下面又有柴沟集、丘家大村,现如今还能找到些许当年的遗迹,不过大多村落也都改头换面,什么小溪桥梁、五龙河风景……这些记载你要真让历史学家一一考证,八成会跑偏。
焦家庄子更有意思,名字里那个“子”字,明清志书、民国行政区划、人民公社变化,一直到龙都街道,如今还没变。明明早年属于吕标乡,行政区划调整几年一折腾,村社归属几度变迁。可村民身份认同反倒不怎么褪色。村落认同,难道不是比所谓行政归属更牢靠些?

只是具体到细节,有的村名从来没正儿八经对过号。比如有些社里头一个村出现两个刘家庄,明代分家、清代并村,后头就理不清了,你要是执着搞清楚今昔对比,反倒容易陷迷宫。历史考据,有时候就是这么吊诡。你硬说盛衰是天意,转年又觉得是人力,这两说法谁都说得过去。总有村落因遗忘冷落成段落边角,偶尔亮相,也只是族谱某页里发黄行文的一抹残影。
数据呢?现在的互联网资料也有用。2019年,诸城徐家洼整体搬迁枫香湖畔怡锦园,正儿八经记得的也就剩下明丘橓墓在五里冈上。你说这变化算是进步吗?城市化浪潮里,老村被拆迁,族谱上记了一百年、两百年的村名字一夜之间没影了,有些人是会感慨的。可本地人说不定根本不当回事,还觉得新小区大高楼才叫“兴盛”。不是谁都醉心于历史,更多人还是考虑自己能不能在新地界混口饭吃吧?

人口的盈缩,社会的更迭,权威史料记多少,终究落在村民柴米油盐的小日子上。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口气。明清官修,永远是新官上任忙着清户清役,怕漏了哪个逃丁漏社;现在的网民可能更关心自家楼下小区的“业主群刷屏”、“谁家小区门口的快递柜坏了”。时代变了,但那种“天地之间,村社更替”的底色,在这里就是这么过来的。
要说当地沉淀下来的 “门道” 那还真是多,每一个名字后头都有章有典,地名变迁、村落兴衰,甚至是明清老志的注脚、现代网络影像的补充,拼拼凑凑都不全。你要按数字分析,不靠谱;多角度看,似乎哪种说法都能成立。地理、历史、心理、传承,全堆在一起,齐鲁大地的生土气息还真不和别的地方一样。

长这么大,哪座村社没点混杂?不是每个社都能一眼望到头。只有真正走到跟前,坐在老槐树底下听两句唠叨,看看新楼旧屋的交错,或者在集市小摊上吸口羊汤锅的气味,才会明白诸城的八乡里社,不就是我们这世世代代在这片地头折腾出的生活印记吗?
这些村村社社,各有各的运气和前因后果,一纸老志未必写得清,人心里多少都有数。不是非要较个真。历史像个不太服帖的老顽童,一会儿跳脱,一会儿又拘谨,反正,诸城的故事,就在那里,不怕人问,也不怕人忘。




